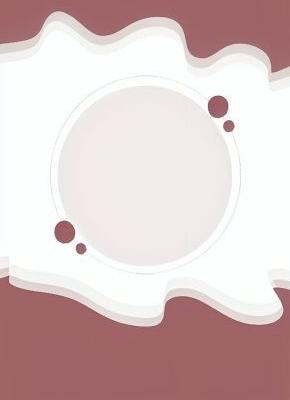1:暗夜,将军府尸横遍地,一百三十二口惨死血泊之中寒夜,北风如刀。
昔日车马络绎不绝的镇北侯府,此刻被冲天的火光与刺鼻的血腥气笼罩。
五岁的凌昭被乳母死死捂在怀里,藏在假山狭窄的缝隙中。缝隙外,是他熟悉的一切在崩塌。
他透过石头的间隙,眼睁睁看着府中上下一百三十二口——从他敬若天神的父亲镇北侯凌啸,
到总是偷偷塞糖给他吃的厨娘张婶——一个个倒在血泊里。那些黑衣杀手刀光闪过,
带起的是一蓬蓬温热的血,映照着他瞬间失去所有色彩的瞳仁。他发不出任何声音,
牙齿深深陷进乳母的手掌,尝到了咸涩的血腥味。
他记得父亲最后看向假山方向的、那充满绝望与希冀的一瞥。杀戮渐息,纵火声起。
乳母抱着他,趁乱从狗洞爬出,在冰冷的长街上亡命奔逃。身后,是他曾经的家,
在烈焰中化作一片修罗地狱。“少爷,记住他们!记住今晚!”乳母的声音嘶哑如破锣,
字字泣血。凌昭没有哭,只是死死地盯着那片火光,将那冲天的仇恨,一点一点,
烙进了骨髓里。三个月后。将军府邸,气氛森严。曾经的副将,如今的镇国将军秦岳,
高坐主位,一身锦袍也掩不住行伍的杀伐之气。
他打量着堂下跪着的、瘦骨嶙峋的孩童和面色惨白的妇人。“你说,他是侯爷的远房侄儿,
名叫谢诚?”秦岳的声音听不出喜怒。“是,将军。”乳母以头抢地,声音颤抖,
“侯爷蒙难,家族零落,唯有此子……求将军看在往日情分,给他一条活路!
”秦岳的目光如鹰隼般落在凌昭身上,带着审视,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算计。“抬起头来。
”凌昭依言抬头,脸上是符合这个年龄的惊惧与茫然,唯有眼底深处,是一片死寂的冰原。
秦岳看了他半晌,忽然笑了,那笑意却未达眼底:“凌兄待我恩重如山,他的血脉,
我自当视若己出。从今往后,你便留在我府中吧。”他顿了顿,一字一句,
如同给一件物品打上烙印:“我赐你新名——秦忠。望你日后,忠于我秦家,
莫负我今日收养之恩。”秦忠。凌昭(谢诚)垂下头,将所有的屈辱与杀意死死摁在胸腔里。
他用尽全身力气,让声音听起来稚嫩而顺从:“谢……谢将军赐名。秦忠……记住了。
”这一刻,五岁的凌昭死了。活下来的,是带着血海深仇踏入龙潭虎穴的——秦忠。
2:刀尖舔血的日子,碎砚探底踏入将军府,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。
朱漆大门在身后缓缓合拢,发出沉闷的巨响,仿佛隔绝了过往的一切,
也隔绝了作为一个“人”的资格。府内亭台楼阁,雕梁画栋,比之记忆中被焚毁的镇北侯府,
更多了几分暴发户式的炫耀与堆砌,少了几分沉淀下来的威严与厚重。凌昭,不,
现在是秦忠,被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嬷嬷引着,穿过一道道回廊。
下人们投来的目光混杂着好奇、怜悯,以及更多的不屑与审视,像无数根细密的针,
扎在他看似单薄脆弱的脊背上。他被安置在西院最偏僻的一间厢房里。这里久无人居,
推开门的瞬间,一股混合着霉味和尘埃的阴冷气息扑面而来。家具简陋,
只有一床、一桌、一椅,窗户纸也有些破损,北风嗖嗖地往里钻。乳母在将他送到后,
便被秦岳以“安顿至别处”为由带走了,他甚至没能再跟她道别。
最后一个与过去相连的纽带也被强行斩断,他真正成了这偌大府邸里,一座孤岛。
独自站在房间中央,五岁的孩子,身影在空旷中显得格外渺小。他没有哭闹,没有呼喊,
只是缓缓走到窗边,伸出小小的手指,轻轻触摸那破损的窗纸。冰冷的触感从指尖传来,
让他因仇恨而灼烫的头脑稍微冷静。他借着缝隙看向外面灰蒙蒙的天空,
眼底那片死寂的冰原之下,是汹涌的暗流。
他从怀里摸出一块尖锐的小石片——这是逃亡路上,乳母给他防身,也是他唯一藏住的东西。
他蹲下身,在床腿最内侧、最隐蔽的木质角落里,用尽全身力气,刻下了一道深深的竖痕。
第一笔。为父亲,为母亲,为那一百三十二道亡魂。刻完,他将石片藏回怀中,
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,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怯生生的、任人摆布的神情。接下来的几天,
风平浪静。没有人过多关注这个新来的、沉默寡言的“养子”。
送饭的仆役将粗陋的饭菜放在门口便转身离去,连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。秦忠默默地吃,
默默地观察。他记住了通往主院、书房、厨房、侧门的每一条路径,
记住了几个主要管事嬷嬷和护卫头领的面孔和大致活动规律。他知道,秦岳在观察他。
那种无处不在的、冰冷的视线,如同潜伏在暗处的毒蛇。他必须做点什么,
来验证秦岳的戒心,也来为自己确立一个“安全”的形象。机会在他入府第七天的下午到来。
那天,秦岳难得有闲,召了他去书房“说话”。名义上是关心,实则依旧是试探。
书房里燃着昂贵的沉水香,书架上摆满了精装典籍,墙上挂着名家字画,一派文雅气象。
但秦忠一眼就瞥见,书案一角,随意搁着一方雕琢古朴的紫金石砚,
砚边还放着一柄装饰华丽的短匕——那是北戎贵族喜爱的样式,绝非中原常见之物。
秦岳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,漫不经心地问着他一些关于“家乡”、“过往”的问题。
秦忠按照与乳母早就套好的说辞,磕磕绊绊,半真半假地回答着,眼神怯懦,
手指紧张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。“嗯,也是个可怜孩子。”秦岳似乎失去了兴趣,挥挥手,
“罢了,日后在府中安心住下,要懂得规矩。”他随手拿起书案上的一卷兵书,不再看他。
秦忠垂着头,小声道:“是,将军。”他慢慢后退,似乎因为紧张,脚步有些踉跄。
在退到书案附近时,他的衣袖“不经意”地拂过了案角。“哐当——!
”一声清脆刺耳的碎裂声,打破了书房的宁静。那方价值不菲的紫金石砚,
摔落在坚硬的金砖地面上,瞬间四分五裂!秦忠似乎吓傻了,呆呆地站在原地,
小脸瞬间变得惨白,连呼吸都停滞了。他能感觉到秦岳的目光骤然变得锐利,
如同实质般钉在他身上。“混账东西!”秦岳猛地一拍桌子,声如雷霆,“毛手毛脚!
可知这方砚台乃是御赐之物?!”巨大的威压扑面而来,带着久经沙场的血腥杀气。
若是寻常五岁孩童,只怕早已吓得魂飞魄散,嚎啕大哭。秦忠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,
几乎要撞碎肋骨。但他强迫自己抬起头,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,
充满了纯粹的、不掺一丝杂质的恐惧和绝望。他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
小小的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。
“将……将军……饶命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他语无伦次,涕泪齐下,
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因闯下大祸而崩溃的孩子。秦岳死死地盯着他,眼神阴鸷,
似乎在判断这究竟是意外,还是某种拙劣的试探,或者……仅仅只是一个蠢货的无心之失。
书房内的空气凝固了,时间仿佛被拉长,每一秒都如同在油锅中煎熬。许久,
秦岳脸上的怒容慢慢收敛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、令人捉摸不透的神色。
他缓缓坐回椅子,手指敲击着桌面,发出笃笃的轻响。“罢了。”他最终开口,
声音恢复了平静,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嘲,“一方砚台而已。念你初入府,不懂规矩,
这次便饶过你。”他挥了挥手,像驱赶一只苍蝇:“滚出去。自有管事教你府里的规矩。
”“谢……谢将军!谢将军不罚之恩!”秦忠如蒙大赦,磕了个头,连滚爬爬地退出了书房,
背影仓皇狼狈到了极点。直到走出很远,彻底脱离了秦岳的视线范围,
他才靠在一处冰冷的廊柱下,慢慢停下脚步。他抬起袖子,用力擦去脸上的泪水和鼻涕,
那双刚刚还盛满恐惧的眼睛里,此刻只剩下冰冷的清明和一丝计谋得逞的锐光。成功了。
他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笨拙、怯懦、容易掌控,并且会因为一点“恩惠”而感恩戴德的棋子。
摔碎那方砚台,既是试探秦岳对他“容忍度”的底线,也是主动递上一个“把柄”,
让秦岳觉得可以随时拿捏他。更重要的是,他确认了秦岳与北戎之间,
必定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——那柄北戎短匕,就是无声的证据。当晚,
他被管事嬷嬷严厉地训斥了一番,并被罚抄写《弟子规》十遍。他趴在冰冷的桌子上,
就着昏暗的油灯,一笔一划地写着,字迹歪歪扭扭,
符合一个“未受过良好教育”的孤儿的身份。夜深人静,月光透过破旧的窗纸,
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秦忠躺在床上,毫无睡意。他再次摸出那枚石片,在床腿内侧,
那道竖痕旁边,又用力刻下了一道。第二笔。为今日之辱,为他日之偿。
月光映在他稚嫩却毫无表情的脸上,那双眼睛在黑暗中,亮得惊人,仿佛蛰伏的幼狼,
正在舔舐伤口,磨砺爪牙,等待着撕碎敌人的那一刻。将军府很大,夜还很漫长。他的路,
才刚刚开始。3:只是个没用的废物碎砚风波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,漾开几圈涟漪后,
迅速归于平静。府中下人看秦忠的眼神,除了原有的不屑,
更多了几分“果然是个惹祸精”的鄙夷。秦忠对此浑不在意,
他甚至乐于维持这种“愚笨怯懦”的形象,这能让他更好地隐藏在阴影里,观察,等待。
真正的麻烦,来自于秦岳的独子——秦昊。秦昊年长秦忠两岁,
继承了其父的高大体格和嚣张气焰,却远未学会秦岳的城府与隐忍。在他眼里,
这个突然冒出来的“野种”,分走了父亲本就不多的关注,
更占据了他“将军府唯一少主”的名分,尽管只是个养子名头,也足以让他如鲠在喉。
秦忠入府半月后,在一个午后,麻烦如期而至。他正按照管事的要求,在院子里清扫落叶。
秦昊带着几个跟他年纪相仿、同样衣着华贵的跟班,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,
故意踩在秦忠刚刚扫成堆的落叶上,弄得一片狼藉。“喂,小野种!”秦昊双手抱胸,
下巴抬得高高的,用鼻孔看着秦忠,“听说你把我爹最喜欢的砚台打碎了?”秦忠停下动作,
握着扫帚的手指紧了紧,随即又松开。他低下头,声音细若蚊蝇:“……是我不小心。
”“不小心?”秦昊嗤笑一声,上前一步,猛地推了秦忠一把,“我看你就是个丧门星!
克死了自家人,现在又来祸害我们秦家!”这一推力道不小,秦忠踉跄着后退几步,
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疼痛传来,但他脸上依旧是那副逆来顺受的惶恐。
旁边一个跟班起哄道:“昊哥,听说这小子没爹没娘教,肯定啥也不会,笨得要死!
”秦昊眼珠一转,脸上露出恶劣的笑容:“说得对!废物就是废物!这样吧,
”他指着院子角落放着的一对石锁,那是护卫们平日练力用的,最小的也有二十斤重,
“你去把那石锁举起来,举过头顶,今天这事就算了。举不起来,就从小爷的胯下钻过去,
再学三声狗叫!”哄笑声顿时响起。那几个跟班兴奋地围拢过来,等着看笑话。